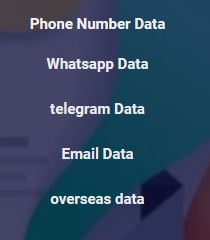在我的人生时间轴上,生过的三个月空白期。这段时间再也无法被回忆或追忆。从2018年2月21日到2018年5月26日,这段时间在我的人生故事中已不复存在。因为这段时间,是我在跳入泳池救下溺水儿子后失去的。让我来解释一下,他反过来又如何拯救了我,让我免于沉溺于社交媒体成瘾。
上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,我和妻子、儿子去拜访了几个大学朋友。奎因就像过去三年里每年一样,喜欢上了游泳池——嗯,就像鱼儿喜欢水一样——而且每次都变得更勇敢一些。
这天,泳池里挤满了从四岁(奎因的年龄)到十七岁的孩子,偶尔还能看到一些四十多岁的家长。我刚从泳池出来,洗完澡,穿好衣服,回到泳池边,就看到奎因正摇摇晃晃地抓着一张充气椅。我冲他喊道:“奎因,你不应该坐那张椅子。去玩内胎吧。” 他照做了,因为他知道自己刚刚因为没有听从之前的指示而被抓了,因为他之前没有听从哪些漂浮设备可以使用,哪些不可以使用。
我坐在离他大约15英尺远的座位上,看着他踢向最近的 乌克兰电报号码数据库 内胎,穿过两三个孩子,进入深水区(也就是整个泳池,除了奎因的入水台阶)。在转换过程中,我看到奎因的手滑了一下,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掉到了内胎下面,从他的位置根本抓不住任何东西。他的头很快就没入水中,他开始抓什么东西——什么都抓。
我站起身,走向泳池边——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他。奎因的头在水面上上下晃动了几次。然后,我跳进水里,把他从泳池里抱了出来,他的头才终于浮了起来。我抱着他颤抖的身体走向泳池边,他妈妈正在那里等着他。妈妈一上岸,他立刻扑进妈妈的怀里,哭了起来。
我的数字死亡
当我蹚向台阶走去时,我才意识到自己刚刚跳进泳池,身上全是衣服——短裤、衬衫、钱包、手表和手机。现在,在我那条浸满水的百慕大短裤的前口袋里,装着三个月来的照片、视频、短信、录音和私人笔记,它们都快要窒息了。
我赶紧上楼用毛巾擦干身体。刚出水的几分钟里,设备看起来还不错。事实上,我儿子那张贴着壁纸的脸正从主屏幕上朝我微笑。但几分钟后,它就输掉了这场短暂的战斗——连同我自二月初以来用数码相机记录下来的所有精彩瞬间。
至少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。
但现在,当我把手机放在装着“本大叔大米”的特百惠盒子里,在一张废纸上手写这篇博客时,我开始理解生活中的一些事情——无论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。以下是我迄今为止发现的东西。
首先,看到自己如此爱儿子,我感到无比欣慰。并非我心中有任何疑虑,而是这样的时刻,才让我感受到这份爱有多深。回想这段经历,我从未停下来思考是否应该投入其中,甚至从未想过是否应该先做些准备。这一切都只是出于本能的需要,我为自己的回应感到自豪。
其次,我发现自己有多么爱我的手机。事实上,说实话,没有了手机在身边,我现在感觉有点戒断反应。(坦白说: 我一时想不起“戒断反应”这个词,我第一个念头就是用 Siri 搜索它。)我对手机的依赖程度,以及我们之间的熟悉程度,都让我感到困扰。该死,就在救了奎因之后不久,我的下一个念头就是我刚刚在手机里失去的生命——当时我走出泳池,把它举过头顶,希望潮湿的空气能瞬间把它吹干,或者上帝能怜悯它的电路板。这太荒谬了,这也暴露了我对手机的荒谬喜爱。
第三,我不认为二月到五月之间的所有经历都已永远消失,我接受它们依然活在我的记忆中这个事实。它们并没有全部消失在我湿透的设备上。你知道在 Facebook 照片里是谁在吃佛陀碗吗?是我。在 Instagram 视频里,站在我儿子旁边看着他来回飞舞的是谁?同一个人——我。事实上,我的身体里真的有一台记录器,它能看到、听到、触摸到、闻到和尝到这个世界,把它记录下来,以便在以后的某个时间点回忆起来。这是我的记忆。虽然它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失去它的力量,但它也不会在我每次跳入水中时短路。我必须更多地使用它。
第四,我必须比以往更加活在当下,感受生活。不知从何时起,我曾试图让自己的思维模式变得不再需要关注当下,因为无论发生什么,都会被保存下来,留待日后再去体验。结果,我所生活和体验的世界变成了我所谈论和描述的世界。我所经历的越来越少,而记录的却越来越多——为了自己,也为了别人的点赞、评论和表情。于是我错过了此时此刻。
- Board index
- All times are UTC
- Delete cookies
- Contact us